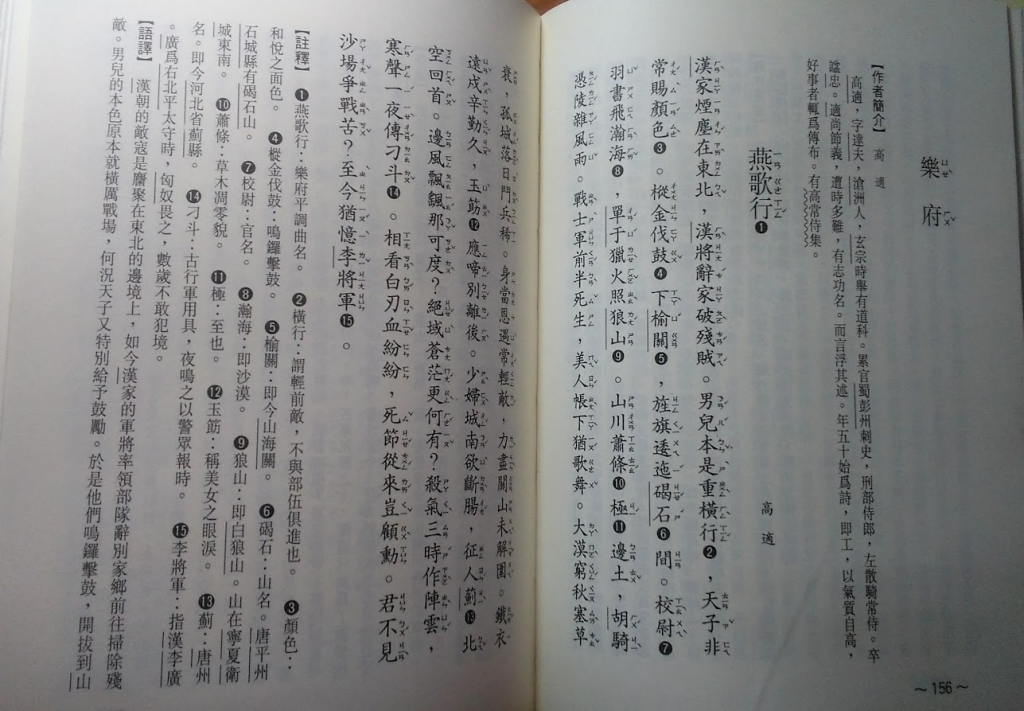
延續昨天的話題,白真陁羅為何不惜「假以守珪之命」、「詐稱詔命」,堅持引戰?
綜觀《舊唐書.張守珪傳》記錄的幾場戰役,張守珪通常採取敵不動我不動的原則,如果非戰不可,多半也是基於「率眾救援」、「突厥又寇北庭」、「板堞才立,賊又暴至城下」之類的防禦動機。
把用兵的頻率降到最低,這是張守珪的武德。張守珪之所以能「每戰皆捷」,在於那些「戰」並不是暴力競賽,而是向毀約方強調尊重界限的重要性,雙方嘗試藉由「戰」,重新建立往後互不相犯的默契。
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的時候,塞外不太安定,「契丹及奚連年為邊患」,從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,契丹和庫莫奚均未再出現逾越舉動,就某個角度來看,算是處於休戰狀態。
各過各的生活,不就是一種和平嗎?可是,對白真陁羅而言,長久的和平是否意謂著他的表現機會從此止步了?
倘若白真陁羅想要晉陞到像張守珪那樣高的位置,勢必得累積很多「戰功」才行。眼看塞外越來越平靜,白真陁羅可能興起了賭一把的念頭。
關於這場賭局的結果,《舊唐書.張守珪傳》寫的是「初勝後敗」,《新唐書.張守珪傳》寫的卻是「知義與虜鬥,不勝,還」。兩者乍看稍有出入,其實意思差不多,《新唐書》或許將「初勝」解讀為勝之不武。
而且,此次不僅「敗」在戰場,更「敗」在心上。
庫莫奚族和朝廷之間好不容易搭起的信任感,被硬生生地搞砸,又回到充滿猜疑的原點。
